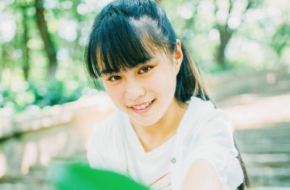解密:朱棣建大报恩寺塔是为了“报恩”还是“忏恶”
永乐皇帝朱棣建造的大报恩寺塔曾在秦淮河畔雄踞了四百余年,是明代南京呈献给世界的“天下奇观”。但这座“中国之大古董”也让后人质疑朱棣建塔的目的,并不是他说的要报答朱元璋和马皇后的养育之恩,而是一些有识之士所说的“忏恶”。
朱棣之残暴胜过朱元璋
历史上,朱元璋以残暴著称,他的残暴很大程度上是严惩腐败的一种手段,而朱棣的残暴则完全是“顺我者昌,逆我者亡”。当他率“靖难”之师从北京打进南京城后,随之而来的是一场极其恐怖的杀戮。其残暴之烈、用刑之酷超过其父。
清初著名思想家、文学家戴名世说:“明成祖之恶,极矣。创为刳、剔、割、剥之刑,施于忠臣义士。”(《忧庵集》)“刳”指剖膛挖心,“剔”为削肉刮骨,“割”指断舌抉齿,“剥”为剥皮楦草。如此种种,皆令人发指。
人称“天下读书种子”的方孝孺,因为不肯为朱棣撰写即位诏书,被灭“十族”。追随建文帝的忠臣义士没有一个能逃出朱棣的魔掌,甚至他的一些兄弟和皇亲国戚也难以幸免。朱棣还制造了“瓜蔓抄”这一历史奇冤。
景清是洪武十八年(1385)的榜眼。不少文章都说他的被杀是因为他身藏利刃上朝刺杀朱棣。但正德朝的宰相王鏊在《震泽纪闻》中记载不同:“文皇(指朱棣)渡江,驻金川门,百官出迎皆拜伏,独清植(直)立,骂不已……乃命左右抉其齿,且抉且骂。顷之,近前若有所启,则含血直沁上衣。遂醢之。”
醢,是将人剁成肉酱的酷刑。但朱棣仍未解恨,“命籍其乡,转相攀染,至数百千人。谓之‘瓜蔓抄’,其村,今为墟焉。”因为景清不归顺,就将他剁成肉酱;又因为一个景清,便杀了全村人。说朱棣是恶魔不为过。
朱棣还将那些忠臣义士的妻妾女媳,押送军营供士兵轮奸;或发配到教坊(妓院),或赏给象奴(饲养大象的蛮人),任人蹂躏。明沈德符《万历野获编》卷十八就记载:“永乐初,发教坊及浣衣局,配象奴,送军营奸宿者,多黄子澄、练子宁、方孝孺、齐泰、卓敬(均为建文帝的忠臣)亲属。”
《告天文书》的内心流露
朱棣由于杀戮惨烈,负罪深重,常梦见景清等人追逐索命,因此惊恐而醒,寝不安席。明末张岱有这样的诗句:“文皇践祚数十年,未得一日安稳卧。”
清乾隆四十二年(1777),有樵夫在紫霞湖附近的山顶挖出两块石碑,某中一块是明代朝天宫道士刘渊然(道教长春派的创始人)奉朱棣的圣旨,为其登基举行“祭天”大礼时,祷告天神祈求保佑的文书刻石,称“告天文书”。这两块石碑后被官府送到朝天宫,藏在玉皇大帝像座中。清道光年间重修朝天宫时又被发现,时任两江总督的陶澍还为两碑写了跋文。
朱棣的《告天文书》中有这样的话:“手足且伤于前后,情怀有恸于死生。骨肉相残,几致屏翰之倾替;腹心构讼,幸兹家国之安全。”这段告白可说是他对杀戮忠良、“骨肉相残”内心忏悔的流露。所以金陵乡贤甘熙说:“观其文词,知文皇当日亦深有负疚于心矣。”(《白下琐言》)
朱棣的“负疚于心”还有一事可说。永乐二十二年(1424)的殿试,照例由皇帝亲自决定状元、榜眼、探花。考官们把推荐的三份试卷先后念给朱棣听,朱棣觉得写得都很好,点头同意。考官们拆去试卷上的封条露出考生姓名,呈给朱棣过目,以便填榜,布告天下。第一名状元名叫孙曰恭,第二名榜眼名叫邢宽。
古时书写是从上到下直书。孙曰恭三字中的曰、恭两字写得靠近,加上朱棣老眼昏花,看成了“暴”字,孙曰恭成了“孙暴”;而邢宽的邢字又与刑字同音,听起来就是“刑宽”,其意即宽大用刑。这触动了朱棣的内心痛处,他大声说道:“本朝只许‘邢宽’岂宜‘孙暴’!”尽管大学士杨士奇及其他大臣一再解释,朱棣仍然认为“孙暴”不如“邢宽”名字好听,用朱笔点邢宽为第一名。(事见明江盈科《雪涛谐史》)
藉佛力以忏除恶业
朱棣通过残暴的杀戮攫取最高权力后的第二年,便下令建大报恩寺;永乐十年,又建大报恩寺塔。一些有识之士认为朱棣建塔名为“报恩”,实为“忏恶”,也就是欲借佛力消弭心中杀伐过重的罪恶感。
“寺名报恩,报何恩欤?昔人诗云:‘九级浮屠篡逆灯。’噫!难逃一字也。”(《金陵待】征录》)金陵乡贤金鳌说的这“一字”就是“篡”,而篡权、篡位必带来血腥的杀戮。
比甘熙、金鳌说得更直白的,是清中期的两位著名诗人程晋芳和陈文述。程晋芳有一首《报恩寺》诗,其中有两句:“杀运乍终宜忓悔,慈恩难报托虚无”。陈也有《登报恩寺浮屠》诗:“靖难师来孰闭门,孝陵云树黯消魂。忠臣已尽神孙死,却建浮屠说报恩”。
陈文述还在诗序中说:“永乐之为此,殆自知杀戮过重,藉佛力以忏除恶业耶。”先贤们的共识,应是对朱棣建大报恩寺塔的深层解读。